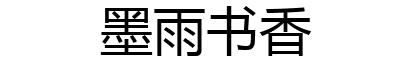(上)
灿恬转学了。
她的父亲,托了很多熟人,终于可以将她转学到成都的一所以艺体见长的高中。她可以有更好的条件学习音乐,为她的高考铺一条更好的路。
她爸爸开着车到学校来接她走,我站在校门口,平静地和她拥抱,平静地看她上车,平静地挥手道别。汽车卷起一缕尘土,缓缓离开。这样煽情的场面,未免也太像电影片段。
明明早已习惯这样不断的失去,为何当我转身之时,仍然有泪滑落。
灿恬,相见终有时。我们不得不继续在自己的生活中奋力行走,而那些在彼此天空中留下的明亮色彩,刻骨铭心,不会褪却。
梦想其实一直很清晰。文阿姨,远在北京的文阿姨,不知为何,妈妈在这些年辗转之中,渐渐竟然与她失去了联系。她种在我心中的小小火苗,却从来未曾熄灭过,反而愈发地燃烧起来。我会去北京。我会站在文阿姨面前,让她看到,当年喜欢问她各种各样问题,飞奔向她夸她真漂亮的小麟儿,已经长大。
我在晚自习结束后继续用更长的时间留在教室,专注地做题,专注地思考。许夏和我有一样的习惯。有时候他会吹口琴给我听,各种各样的旋律,宛若天籁。
我们在每个夜归于寂静的时候一起离开教室。他细心地关好所有的灯,锁上门,然后走在我的右边。我们很少聊天,更多的时候,是沉默地走过寂寞的校园,在我的宿舍楼下,互道晚安。
我喜欢这样的晚上,让白天喧腾的心在无言中静静地沉落,覆盖疲惫的一切。只有当我们走到宿舍楼前,看见宿舍楼洒得遍地都是的灯光时,我才会猛然感到残酷的真实。有种东西被这明亮刺眼的灯光倏地打碎了。
高三的寒冬很冷,匆匆的脚步似乎无暇去体会寒冷的滋味。清晨总是黑暗的,见不到一丝光亮,黑暗得让我总有莫名的恐慌。
那个冬日的清晨发生的一切,像是一出早已导演好的剧,任何人都没有力量改变剧本,我只能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参透剧本安排的意义。
深冬,天未亮,寒风刺骨。我和每天一样,提前来到教室读书,等待晨跑的铃声。晚睡早起的生活让我感到浑身充满力量,绷紧的弦,一日也不能松断。
铃声响起,同学们在操场上开始集合,准备晨跑。我关了教室门,下楼。动作稍微慢了一点,快到操场时,看见大家已经集合完毕跑了起来,我有点着急,直接从操场边的台阶上跳了下去。
我没有看到脚下的那块大石头。我的脚不偏不倚地触到了石头上,我听到脚踝发出奇特的声音,整个人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剧痛让我的眼前变得黑暗,只能隐约看到有好多人向我跑来,他们围住我,关切地询问。我艰难地说出“帮我找高三文科(1)班的同学”,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出租车上。我的头放在昕昀的腿上,脚放在周老师的腿上。他们小心翼翼地护着我,焦急地催促司机开快一些。右脚的剧痛无比清晰,我没有流泪。早已安排好的游戏与捉弄,无泪可流。
昕昀见我醒来,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亦用力抓紧紧她的手,想让她安心,半天却没能挤出一个微笑。
在弥漫着我不喜欢的味道的医院,我看到我的右脚踝已经肿得像个馒头。医生拿着粗大的针管替我抽出淤血,我抓疼了昕昀的手臂,哇哇大哭。我已经记不清楚我有多久没哭了,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没有办法再忍了。
我的右腿膝盖以下被打上厚厚的石膏。我坚持回学校。我不能住院,我不喜欢医院的味道。更重要的是,我不能浪费掉我视如生命的时间。
“林麟,只要你能够坚持,相信一切困难都可以解决的。”周老师如此理解我,他迁就了我的固执,背起我,带我回学校。
许夏站在我的宿舍门口。男女生的晨跑是分开的,我们班的男生在另外一个操场晨跑,因此他没能在第一时间知道我出事。当他看到我时,他的脸上布满了惊讶。他显然没有料到他会看到一个右腿打着厚厚石膏动弹不得的林麟。他手里还拿着医务室的袋子,里面装着各种的跌打药膏。
我笑了起来。刚刚应该是体育课,他一定是在打完篮球后匆匆赶来,左手抱着球,右手拿着药袋子,脸上流着汗,不知所措地看着我。这个样子的许夏,我还真是从来没有见过。
“怎么这么严重?打了石膏?你怎么不住院?”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却并不期待我的回答。他对周老师说:“周老师,你们等一下,我回宿舍把球放下,洗把脸,我来背她!等我,一定不要让其他人背!”说完就跑走了。
当他在我面前默默弯下腰,我突然有流泪的冲动。那是多么宽厚的脊背,它能承载些什么?
那一个冬天,与以下几个词息息相关:石膏。右脚。许夏。昕昀。爱。
我在许夏的背上度过整个冬天。教室,宿舍,两点一线。他和昕昀轮流从食堂给我打饭,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偶尔许夏不在的时候,昕昀也背过我。我根本难以想象她是怎么用她瘦弱的背将我一步步背下楼梯。
长时间的不能自由活动,让我的脾气变得愈发暴躁沉郁。在教室里我只能坐在周老师为我特制的位置上,右腿平伸,这使我写字变得困难。在宿舍我需要昕昀为我做一切事情,每次穿衣脱衣,都会花去她很长的时间。就连上厕所,我也不能离开昕昀的帮助。我偶尔会暴怒,会莫名地向我最亲近的这两个人发脾气,无理取闹,而许夏和昕昀,无条件地纵容着我,近乎宠溺。
许夏每过一周背着我去医院检查。在一次检查归来后,我突然地烦闷起来,在他背上大吵,要他放我下来,我要走路。他当然不会依允,自顾自地背着我走进校门。
后来我终于安静下来。因为许夏背着我一步一步地上台阶时,我在他的背上,看到他浓密的头发,听到他显出疲倦的呼吸。我的心柔软地疼了一下。有泪落下,滴到他的肩上。
圣诞节,每个班热热闹闹地准备开晚会。我无法参与到其中,在周老师的办公室里做着习题。周老师为我准备的小暖炉非常温暖,躺椅非常安逸,做题做累了,我便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朦胧中听到有人推门进来。熟悉的脚步和气息让我知道,是昕昀。我没有睁开眼睛,想知道她要做什么。
她轻轻放了东西在桌上,然后在我身边坐下。片刻,她将烤得暖暖和和的一条毛巾,轻轻裹在我打着石膏容易冰冷的右脚上,用手捂了很久,确定已经很暖和,才轻轻拉开门走了。
有一种细腻微小的感动在心中无止境地弥漫开来。我睁开眼睛,鲜艳欲滴的红色映入眼帘。是一大捧康乃馨。纯粹的红色。它们肆无忌惮地开放在我面前,像是这个冬季从天而降的使者。在它们的旁边,是一个毛绒绒的机器猫,它无比灿烂地笑着,万能的口袋里装着一张纸条:亲爱的麟麟,圣诞快乐。
哦,我的天。
这并不是周末,昕昀是怎样给我变出了这样一束康乃馨和一个可爱的机器猫?
晚会之前,昕昀和许夏来办公室背我去教室,我才知道,我那一向淑女温柔的昕昀,跟着许夏和其他一些想上街买东西的同学一起,翻了学校的围墙出去,只为送我一份圣诞礼物。翻回来的时候,不慎闪了腰。
我揉着我亲爱的昕昀可怜的腰,大笑着却掉了泪。
“昕昀,下星期你没办法做值日了,让许夏替你包了!谁让他没替我保护好你,竟然带你去翻墙,还闪了腰!”
我们哈哈大笑起来。如此温暖的圣诞节。
那束康乃馨,在半个多月以后,才慢慢凋零。具有生命力的不起眼的花儿,无香,却不影响它的倔强生长。正如拥有的某些情感,在静默中灿烂辉煌。
若时光就此停滞,也算是一个恩惠吧。
春暖花开之时,我终于拆掉了厚厚的石膏。我可以穿着笨重的大棉鞋,一瘸一拐地在校园里行走。我对走路这件事情充满了新奇感,像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高兴不已。
却也有一份怅然若失。再也没有理由留在让我习惯和贪恋的那个宽阔的脊背上了。
然而这个春天,馥郁的气息下面,掩盖着另外的一场始料未及的风波。
非典。这种闻所未闻的疾病,在一夜之间席卷了神州大地。地处四川盆地的我们,幸运的没有受到太大的直接波及,但从媒体上得知的越来越多的信息,让所有人谈之色变。学校紧急地实行了全封闭的政策,任何人不得进出校门,无一例外。
高考之前的最后一段原来就显得紧张的时间,就这样更加平添了几份令人不安的气氛。
校门口每天都有家长排着队来看孩子。隔着一道大铁门,那情形让人很自然地想到探监。没办法,学生不准出校门,家长不准进校门,校门只开了一个小侧门,由几名门卫充当中间站,将家长带来的大包小包传给校门里面的孩子们。
一向感冒不断的妈妈,在凌县二中成为了重点保护和观察对象,一步也不能离开学校。
我们就这样,隔着几百里,遥遥惦记。
脚伤尚未痊愈的我,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即将迎来又一个立夏。我最钟爱的日子。我的生日。
那天,我也成了被“探监”的对象。
舅舅、舅妈、小雪,我在桐州的三个亲人,隆重地举家出动,来看望我了。
他们带了一个硕大的生日蛋糕和一大包各种各样的零食,隔着铁门,祝我生日快乐。舅舅试图给门卫说好话进来一趟,但被严厉地拒绝了,在门外无可奈何地冲我笑。
小雪戴了一个可爱的大口罩,只露出两只大眼睛,在门外蹦蹦跳跳,着急地喊:“姐姐,姐姐,你什么时候能回来陪我玩啊?”我忍俊不禁。这话听起来,我就更像是身陷牢笼失去自由的小鸟了。多想亲亲她的小脸蛋,无奈不能遂愿,只好伸出手去,握握她的小手:“小雪乖,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话哦,多吃饭,千万不要生病。姐姐很快就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