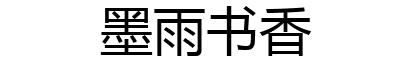(上)
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拉过小提琴。
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矿上包了青花镇的剧院,准备举行盛大的儿童节晚会。杨校长和我的爸爸妈妈商量,问他们能不能让我演出一个节目。
妈妈很意外,虽然我练习小提琴已经将近三年,但是从没在公开场合演出过,她有点担心,不知道我能不能胜任。爸爸倒是很有信心,摸摸我的头,问:“麟儿,想不想上台表演?跟平时拉琴是一样的,只不过台下会有很多人欣赏你的表演,为你鼓掌。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聚集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最棒的!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对吗?”
我对爸爸的描述似懂非懂。表演。我从电视上看见过一些晚会,比如过年时全家必看的春节联欢晚会。台上的人浓妆艳抹,载歌载舞,五彩的灯光灿烂地照亮他们的脸庞。那就是在表演吧?对了,同学来我家玩时,我给他们拉过琴。我还给爸爸妈妈的同事们拉过琴。我还在班里唱过歌。我想,那也算是表演吧?对于爸爸所说的情景,我的心里莫名地蠢蠢欲动,像有着什么积攒已久的情绪在跃跃欲试。我答应了。
我本想拉《梁祝》。那首让我一听钟情,着迷多时的曲子。对于我来说,这难度极高,我反复练习过很多遍,才勉强能将它完整地演奏出来。
爸爸没有同意。他希望我可以有最好的表现,而不是费劲地去做自己力不能及的事情。他为我选择了《步步高》。这首曲子我也非常喜欢,而且是我最拿手的。于是,每天完成原定的练习任务之余,我还会再练习几遍这首我已经非常熟悉的曲子。我怀着小小的激动和小小的不安,期待着六一的到来。
剧院里座无虚席。舞台上的节目精彩纷呈,台下的观众掌声连连。
后台,一片忙乱景象。下一个节目是幼儿园小朋友们的舞蹈《大西瓜》,他们穿着红绿条纹的肥大衣服,看上去像一个个可爱的大西瓜。负责化妆的阿姨手忙脚乱,因为他们一直在不停地相互打闹,一会儿这个的眼睛成了黑眼圈,一会儿那个的口红糊得满脸都是。我被逗乐了,但我不敢笑也不敢动。下下个节目,就是我的小提琴独奏了,另外一个阿姨正在给我化妆。我的眉毛被画得又长又粗,几乎弯到了鼻梁;我的眼睑被涂上了黑黑的眼线,看上去像个大熊猫;我的小嘴巴被涂成了夸张的大红色,我小心翼翼地嘟着嘴,生怕一不注意将口红弄花;最后一道工序,是往我的脸蛋抹上红扑扑的胭脂。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阿姨又将我的稀疏浅黄的头发使劲地拢起来,扎成一个冲天炮的样子,还别上一朵大红花。
我完全不认识镜子里的林麟了。她嘟着红红的小嘴,冲我眨着眼,脸上洋溢着开心的光泽。我于是后知后觉地开心起来。我是小大人了,我和电视里的那些漂亮的姐姐们一样,化了妆,要为很多人表演了!
原来,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是无法看清楚台下的脸庞的。我隐隐约约看到坐在第一排的爸爸妈妈。我的心中充满了温暖,没有丝毫的畏惧。灯光打在我的身上,我举起了琴弓。
这是属于我的时间。我和我的小提琴,早已对彼此无比熟悉。我站在台上,是如此渺小,但我的琴声,响彻了整个剧院。我在一瞬间爱上这种感觉。我仿佛天生地爱恋了舞台。这比一个人在家练琴有意思多了。所有人都在看我,所有人都在聆听,我,是中心。多么美妙。
我比平日更娴熟地演奏完了《步步高》。我甚至意犹未尽。我牢牢记住爸爸妈妈的嘱咐,怀抱我的小提琴,面带微笑,矜持而优雅地深深鞠躬。
掌声如潮。我静静站立,竟然被自己小小地感动了。
那次演出在我生命中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爸爸妈妈看出了我的天赋,看到了我在舞台上的驾轻就熟毫不怯场,看到了音乐给我带来的快乐。从那以后,矿上和镇上的各种各样的晚会,都有我的身影。拉小提琴、唱歌、跳舞,林麟这个名字,在青花镇这个小圈子里,渐渐小有名气。
另外一次重要的演出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让我第一次可以在电视上看见自己。是凌县的国庆节庆祝晚会,我作为青花镇节目组的一员,和其他演员一起,坐了半个多小时的中巴车,前往凌县。那个舞台比青花镇剧院的舞台要大得多。我穿上新疆的传统服装,头发被辫成了无数的小辫子,手里拿着镶满了铃铛的手鼓。我的节目是独唱《娃哈哈》,老师给我编排了一段新疆舞。听说凌县电视台会直播,我丝毫没有因此而紧张,反而更加兴奋。我在这边演出,而爸爸妈妈可以在家从电视上看到我,这简直是太美妙的事情了。
那天,我超常发挥,博得热烈的掌声。晚会结束后回到青花,我兴冲冲地赶回家,急切地问爸爸妈妈有没有看到我。他们笑得很开心:“看见了,看见了,麟儿真棒,唱得真好!”
第二天,电视台重播了这台晚会。我们一家人守在电视机旁,等待着我的出场。电视里那个小孩,真的就是我吗?胖乎乎的小圆脸,稚嫩的声音,稍显生硬但不失可爱的舞姿。手鼓上的铃铛随着歌声叮当作响:“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娃哈哈,娃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在我自己的歌声中,我恍然看见,有一个梦想,渐次清晰。我的生命,应该是注定要和音乐息息相关。
有一天,我自己摸索了一会儿后,在没有曲谱的情况下,完整地演奏了《机器猫》的主题曲。虽然只是一些单一的音符,但几乎没有任何偏差。这让爸爸非常惊讶。但我觉得没什么,那是我最爱的动画片和动画人物呀,每天都听,自然而然就能背下它的曲谱了。我喜欢上这个游戏,试着摸索了很多熟悉的动画片主题曲,有时候加点儿想象乱拉一气,也还挺悦耳。
音乐让我变得开朗起来。我不再终日坐在墙角翻看我那一大堆一大堆的画报和拼音读物,有时我甚至可以暂时丢下妈妈给我新买的《机器猫》漫画,听她的话出去跟小朋友玩。
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开始拥有朋友。李辰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没有妈妈,跟爸爸一起来到青花镇没多长时间。她的爸爸,李叔叔,是一个和蔼的牙医,镇上的人都喜欢在他的诊所看牙。我的一颗不听话的蛀牙,就是李叔叔给我拔掉的。我害怕得大喊大叫,但李叔叔温和地哄着我,告诉我只要打了麻药就不疼了。果然,他没有骗我。
李辰是个可爱的小姑娘,眼睛很大,几乎比我的小眼睛大出一倍,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甚是奇妙。她的头发又黑又亮,不像我的头发稀疏松软,整个一个黄毛丫头。她长得很高,我一般都得仰着头跟她说话。我喜欢和她玩,她也喜欢和我玩,所以我们是朋友。小孩子心中对朋友的定义,就是这么简单直白。
李辰爱笑爱闹,很活泼,跟班里每一个同学关系都很要好。在她的建议下,有的傍晚,家住附近的同学们,都会聚到我家里来,听我拉琴,一起唱歌一起玩。除了爸爸妈妈,李辰算得上是我最忠实的听众。她对我的小提琴表现出的浓厚兴趣超出了我所能理解的范围。她曾经轻轻地拨动过我的琴弦,激动得笑了很久。我邀请她试着拉一拉,她却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要听你拉,你拉得好听。”
我深深地记得她对我和我的小提琴的保护。有一个男同学对我不服气,在课间明确地表明了他的观点:“小提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会弹钢琴,钢琴比你的小提琴贵多了,弹出来的曲子也好听多了!”我有点儿发愣,而李辰迅速地冲了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领,脸上是我没有见过的凶狠表情:“你再说一次!回家弹你的破钢琴去,别在这儿找打!”李辰的个头比那个男同学高很多,她的气势显然把他吓坏了,立刻闭嘴回到自己的位置,再也没敢出声。
我感激李辰。我没有她那般的勇气去捍卫我深爱的小提琴。我只能给她拉一首首好听的曲子,用这样的方式来向她表明,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妈妈对我在家里举行这种小型的同学聚会非常赞同。她一直深怕我太过倔强和孤僻。每次同学们来了我家,和妈妈打过招呼后,妈妈就会到她的卧室里去,关上门看书,或是写日记,给我们留出完全自由的空间。同学们都非常喜欢我的妈妈,她像尊重大人一样尊重他们。这也是他们越来越喜欢来我家的原因。而“林麟”这个名字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也成了一张通行证,同学的家长都知道林麟是个品学兼优多才多艺的好孩子,林麟的父母都是学校的老师,自家的孩子和林麟一起玩,大可放心。
哦,但我从来不会因此而自大。相反,我感激同学们。他们和我一起玩,听我拉琴,让我觉得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喜欢有朋友的感觉。在这样的聚会上,我扮演主持人、琴手、歌手,我乐此不疲。我的心灵手巧的妈妈若是有空,还会在同学们到来之前帮我小小地布置一下客厅,比如,在日光灯管上缠一圈薄薄的彩色皱纹纸,这样灯光会变得五颜六色。还会在墙上贴一些亮晶晶的玻璃纸,整个客厅看上去都开始闪光。
妈妈为了我快乐健康的成长,费尽心思,不惜一切。而无知的我怎能体会,那些夜晚,与这一群无忧无虑孩童的天真欢笑一墙之隔的,是一个女人怎样的孤独与寂寥。
我与爸爸之间因音乐而生的亲近,不动声色地悄悄起了变化。对于小提琴,我有了自学的能力,爸爸已经把能教的基本上都教给了我,我的惊人进步使我的小提琴学习不再成为他的约束,我也不再像初学之时心心念念地盼望着他早点回家,教给我新的曲子。我又开始习惯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的夜晚,我忽略爸爸回家的时间,我沉溺于我自己的世界,与音乐和书本相伴相生的世界。
当矛盾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的小宇宙终于发生天大的变化。
那是爸爸妈妈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我面前吵架。周末,妈妈准备带我出去给我买衣服,打开抽屉发现所有的钱都不翼而飞了。爸爸在一旁不吭声,妈妈用满是怒火的目光瞪着他。在我的印象里,妈妈的眼睛是温柔而忧伤的。我见过那双眼睛落下的泪水,柔弱得令人心悸。而此时,它在喷着火。
“现在你连抽屉里的钱都能全部拿走了?那是家里所有的积蓄,一分也没有了,要怎么办,你说啊!”
妈妈的嗓门很大,她很激动。她骨头里其实是一个直白而火辣的女人,在爸爸面前一味的压抑,积攒多时,终于造就歇斯底里。
爸爸理亏,一开始并没出声,闷头抽烟。后来,他没能忍住,没能继续保持沉默,站起来亦大喊大叫:“我就是把钱都拿走了,而且全输了,怎么了?已经输了,我上哪里去找回来?”
我站在我的房间门口,迷惑地看着父母的争吵。这是不曾发生过的一幕。我隐隐约约知道,这和爸爸平时的不归家有关系,和一件名叫赌博的事情有关系。
“咚!“一声闷响,争吵声嘎然而止。三个人的目光变得愕然。
我的小提琴琴盒,从墙上摇晃着掉了下来。盒盖微开,我可怜的小提琴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
片刻的寂静之后,我尖叫着冲了上去,从琴盒里拿出小提琴。弦断了两根。断掉的弦难看地停滞在半空中,看上去茫然无着。它已经再也不能演奏出美妙的音符。我抱着它,欲哭无泪。
我求助地看着我的忘记争吵的父母。爸爸拿过小提琴,眼光黯淡下来。他无可奈何地说:“麟儿,弦断了,是没法修的。它彻底坏掉了,不能再拉了。”
我大哭起来。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向挂得牢牢的琴盒为什么会莫名地掉下来。没有原因。只剩下一个令人难过的结果,坏掉的琴盒躺在地上,像是折了翼的蝴蝶。我无法忍受。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失去一件心爱的东西。虽然年少得甚至不懂得什么叫做心痛,但那种无能为力的难过,像一个诡异的印章,不依不挠地按在我懵懂而敏感的心上。
之后的一段日子,爸爸特意又去过一次桐州,但是再也没有找到过这样的儿童专用二分之一小提琴。他没有再想其他的办法,因为在那个时候,找到一把儿童小提琴本来就很不容易,另外,家里实在也没有多余的钱可以用于这样奢侈而昂贵的开支了。我似乎懂得了,生命中本就存在这许多的无奈,任何事情,不是只要我喜欢就可以永远拥有的。
我与小提琴的缘份就此划下句点。我知道爸爸心里是愧疚的。他拿着他的二胡和我说话时,语气分明是小心的商量:“麟儿,小提琴咱们今后有机会再练。从现在起,爸爸改教你二胡好吗?其实爸爸更喜欢和更拿手的是二胡。它是中国的传统乐器,只有两根弦,但它拉出的曲子,决不比小提琴差。”
我接过那把对我而言显得有点庞大的二胡。我对它并不陌生。我对爸爸拉二胡的样子,同样着迷。他坐在椅子上,将二胡的琴筒放在腿上,手拉动琴弓,音符便行云流水般淌过。他闭着眼睛,随着节奏轻轻摇头,投入而痴迷。
我点头。我要驾驭这两根弦的乐器。我甚至自我安慰道,二胡多好啊,可以坐着拉。的确如此。若说我对小提琴有什么不满之处,便是动辄数小时的站立,让我从三岁起如同对待恶梦般惧怕。
李辰知道这件事后,大哭,分明比我还难过。我不知所措。我感到抱歉。她对我那样好,那样喜欢我拉小提琴,可我以后不能再拉小提琴了。她和我一起失去了这件心爱之物。
后来,我渐渐得知这个在青花镇流传很广的故事。李辰的妈妈,是一个小提琴手。在生下李辰后不久,跟着另一个小提琴手走了。李辰的爸爸带着她来到青花镇,一个人艰难抚养她长大。她妈妈只留下了一个空荡荡的琴盒。于是她从小就以为,小提琴代表了从未谋面的妈妈。只有小提琴,才能填补她幼小心灵的那个空白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