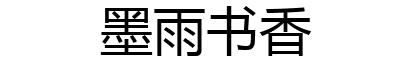(下)
青花把两本中级教师资格证放到林风面前的时候,林风吃了一惊。他翻开其中的一本证书,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贴着自己的照片。青花曾经无数次提过函授和评级的事情,但他从来没有放在心上过。这次,青花竟然神通广大地给拿下了这个证。青花轻描淡写地说:“这次的职称,没有关于文凭的限制了。我和你都符合条件,所以申报了一下,就都通过了。有这个证书总比没有好。”林风心里自知理亏,有些尴尬地说了声谢谢。
不求回报地为林风做任何事情,这已经成了青花的习惯。甚至如果不这样做,她反而会觉得别扭。这次评职称,她倒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林风这两年的工作业绩并不好,学校本来是给了一个为难的态度,不过最终还是结合林风的综合表现,勉强通过了他的中级考核。青花希望拿到中级职称可以对林风的工作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她心底深处,对林风永远抱有希望。
为了开店的问题,她和林风讨论了很久。她主要是考虑到家里开店会不会对林麟造成影响,女儿会不会不理解身为教师的父母开副业的行为。但这个担心很快被证实是多余的。林麟完全理解家里的情况,甚至主动为家里的店分忧。小店逐渐走上正轨,比预想中的情况要好很多。青花更忙碌了,但想到林风欠下的债正在一点一点还清,她心里便只剩下了高兴。
冬天的一个周末,小妹青桃来青花镇看她的大姐。对于自己的这几个妹妹,青花深深浅浅是有歉意的。继青梅初中毕业辍学在村里当了幼儿园老师后,青桃也初中毕业了。建设和建国刚上了大学,家里经济条件不乐观,无力供她上高中。父母没有明说,但她看到了父母眼中的为难,装作很轻松地主动要求上中专。而她,是大家公认的最聪明的幺妹,她的成绩,几乎比当年她的大姐还要更好。
青桃义无反顾地填了桐州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虽然像哥哥姐姐那样上高中考大学是她从小的梦想,但她亦深深懂得什么叫做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助与关爱。就让哥哥姐姐代替自己去实现梦想吧。她只想尽快从中师毕业,像爸爸和大姐一样,当一个优秀的老师,到那时,就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了。
青花在车站接到青桃时,看到这个一向大大咧咧的小妹穿着单薄的棉衣,腿上是一条薄薄的夏天穿的真丝裤,里面连条秋裤都没有穿。圆圆的小脸冻得红红的,笑得很灿烂。青花一阵心疼,埋怨青桃:“这么冷的天,你就穿这么点?冻感冒了怎么办?”青桃乐呵呵地挽住青花:“大姐,你看看我,几乎比你胖了一倍呢,这么强壮的身体,从来就不知道感冒是什么滋味儿!放心吧!走吧,回家,我要看我小外甥女儿!”
青花与青桃年龄差了十几岁,对这个妹妹,她心里有更多的天生的疼爱。而林麟跟这个看上去像姐姐的小姨简直亲热得不得了,成天都把小姨挂嘴边。要不是天冷,非得跟着青花出来接站不可。
青桃陪着麟儿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家里的那台录音机成了姨侄俩共同的玩具,青桃也是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她和麟儿把磁带一盒盒地放进去听,再比赛谁学歌学得更快。两人抢着拿话筒,青桃唱一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麟儿随即唱一首《蜗牛与黄鹂鸟》。比到最后比不出胜负,青桃搂着麟儿哈哈大笑。
她也见到了大姐的辛苦,周末根本没有空闲时间,备课、顾店、做家务,样样事情都不轻松。还好麟儿实在懂事,学习不需要妈妈的任何督促,很自觉地把功课放在第一位。练二胡的时间也是雷打不动,哪怕电视里正在播放她最喜欢的动画片,她也能做到心无旁鹜地坚持拉完当天的练习曲。
夜已经很深,林麟已睡,林风又没有回来。青桃睡在大姐的身边,揣着心事,睡不着。她自从来到大姐家,还没见到姐夫的面。她看着大姐忙前忙后,也不知道要怎么问。她才十几岁,并不能太深刻地懂得爱情与婚姻,但她记得,当年大姐刚带着姐夫回家的时候,脸上洋溢着甜蜜,那时候的大姐,是那样的美,那样的充满活力。可是现在,大姐像是变了一个人,瘦得不成样子,笑容也很少,经常沉默着忙忙碌碌,本还年轻的脊背似乎都已经有些佝偻。大姐是不是并不像经常给家里写的信所说的那样幸福?她想。
青花疼爱地摸摸青桃的头:“丫头,还没睡着吗?”青桃还没来得及回答,便听见青花剧烈地咳嗽起来。青桃很紧张,轻轻捶着她的背,却不起作用。青花示意她拿过痰盂,一口鲜血随即赫然可见。青桃被吓到了,不知所措。她不知道她的大姐发生了什么事,身体有多虚弱,竟然会严重到吐血的地步。青花苍白的脸上勉强挂上一丝笑意,摆摆手,让她不要出声,别吵醒了林麟。青桃于是没有开口,默默地给青花倒来一杯热水。
“姐没事。睡吧。不要担心,乖。”青花关了灯,握住青桃的手。她多想在最疼爱的小妹面前将坚强与快乐伪装到底,可惜终究失败了。黑暗中,冰冷的泪在她脸上划下伤痕。
青桃走的时候,青花坚持从小店的货架上拿了各种各样的零食塞进青桃的挎包。这个挎包,就是青花读初中那年,莲桂亲手缝制的那个让青花无比钟爱的挎包。如今它依然完好,虽然已经旧得看不出来颜色,但青桃仍然像当年的青花一样钟爱这个包。青花抚摸着母亲绣在包上的那朵青花,怔了好久。
送青桃坐上火车,青花独自往回走,心里有淡淡的释然。她往挎包的内层塞了二十块钱,青桃应该要到了学校才能发觉。若是当面给,她定然不会收。这个小妹啊,脾气比哥哥姐姐们甚至更固执。
火车站外的那座石板桥还是像当初刚修好的模样,没有扶拦,看上去摇摇欲坠。而青花知道它其实是坚固的。即使没有林风的手可牵,她一个人,也得慢慢地稳稳地走过这座桥。
小店的正常运营让这个家沉重的经济负担暂时缓和了下来。而没过多久,林麟又出事了。
自幼体弱多病的林麟本来自从那一场篮球风波之后,就不再那么轻易地染上小病了,以前感冒是家常便饭,这两年都很少进医院了。这件事让青花很是宽心。林麟从来就不会吃药,吞不下去那些大大小小的药片。医生又不能总是只开冲剂,每次吃药的时间对一家三口来说就是天大的折磨。林风把药片碾成粉末,盛一勺白开水,加点儿白糖,举到林麟嘴边;青花好说歹说地劝林麟吃药,可任何事都听话的林麟对吃药这件事却是顽强抗拒,坚决不吃。最后都是一人捏鼻子一人硬灌来结束这场战斗,青花累得不行,林麟哇哇大哭。
所以林麟的这一次生病显得太过突然。半夜,青花做了一个恶梦,猛地被惊醒,下意识地跑到林麟的小屋去看她。果然,林麟正捂着肚子艰难地叫着“妈妈”。青花浑身冒冷汗,一把抱起林麟。万幸的是,那个夜晚,林风在家。他被青花叫醒,看到女儿的样子,也差点儿失去主张。他稍微定了定心,抱过林麟,拉开门就冲了出去。青花抓起几件外套,紧跟着跑出去。
寒风中,到医院的路程显得如此漫长。
因为是半夜,镇医院里只剩下几个值班的医生。他们看到冲进来的林风和青花,也吓了一跳,马上通知了几个外科医生赶到医院。等待医生的时间里,青花心急如焚,脑袋几乎一片空白。她不知道上天又将要给她什么样的考验。她只能紧紧抓住林风的手,这样,才能使她的手不要抖得那么厉害。
医生赶来后,很快诊断为阑尾炎。夫妻俩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一个小手术,而不是什么大事。可他们还没缓过气来,医生接下来的话又让他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么小的孩子,我们医院做不了这个手术。快送到凌县医院去吧。”医生拨打了凌县医院的救护电话。接下来,给林麟打了一剂止痛针后,只能等待医院的救护车到来。
漫漫的冬夜,黑暗无边无际。林麟懂事地不再哭闹肚子疼,她强忍着疼痛,反过来安慰束手无措的父母:“爸爸妈妈,打了针后就没有刚开始那么疼了,真的,你们不用着急。”青花镇定下来。女儿现在正是最需要自己的时候,不能显示出惊慌。
此时此刻,横亘在夫妻之间的巨大空白,在瞬间被小小的女儿填补。他们只是年轻的父母,面对女儿的病痛,除了相互依靠,别无选择。
救护车终于来了。在寒冷的半夜,载着一家三口赶往凌县医院。
凌县医院的医生为林麟复诊之后,告诉青花:“孩子得的不是急性阑尾炎,是慢性的。并不一定要用手术来解决。你们商量一下,尽快决定。”
青花一听不是急性阑尾炎,心里又稍微轻松了一点。来的路上,她一想到这么小的女儿得挨一刀,就难受得不行。她赶紧对医生说:“既然是慢性,那就不开刀,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而林风几乎和她异口同声地说出了这句话。
医生看着这对年轻的父母,微笑着说:“不用着急,先挂上点滴,再开几副药吃了就可以了。不过,不开刀就不能根治,她以后还是存在着阑尾炎的隐患,得随时注意。”
这场风波,总算是这样有惊无险地结束了。林麟打着点滴,睡着了。林风趴在病床边,也睡着了。青花本来就经常失眠,在这样的情况下,更是无论怎样疲倦也无法入睡。她看着熬了一夜的丈夫,下巴长出了凌乱的胡茬。不再被病痛折磨的女儿,睡得香甜安稳。这样的情景,令她似乎又忘记了那些孤独的夜晚、带血的咳嗽、冰冷的泪水。她想她终究是无法离开这个男人。哪怕这份爱早已沉重得压弯她的脊背,她也无从舍弃。
文清和洪亮的到来,让青花仿佛看到了多年前背着装满爱的行囊初来青花镇的自己和林风。她不需要任何理由地迅速喜欢上这小两口。文清是个极富才情的女子,和青花毕业于同一个学校的同一个专业,这无疑又拉近了她们之间的距离。
青花很快发现文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子。她和洪亮心里装的那个梦想,大得让青花几乎无法正视。除了思考自己的爱情、思考女儿的成长,青花从来没有思考过更多的问题。她已经认定她的一生将要在与自己同名的这个小镇上安安稳稳地度过,她以为文清也有着与自己刚来青花镇一样的想法。可她错了。
如果说文清和自己在某些方面还有着相似之处,那么洪亮和林风简直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男人。洪亮沉默少言,待人彬彬有礼,偶尔语出惊人。他从来不在外面应酬,规规矩矩地上课,准时回家,一头扎进书堆就出不来。他房间的灯经常亮到凌晨一两点。那所有着如雷贯耳的名字的学校,是青花平时用来激励女儿的工具,她没想到那却是洪亮正在为之奋斗的目标。那座身为伟大首都的遥远城市,离青花镇有着两天两夜火车的路程,是青花连想也没想过亲自去一趟的地方,却是洪亮和文清共同的目的地。青花有些明白了。文清对于青花镇,将只是一个旅人,一个过客。
她对这个比自己年幼好几岁的年轻女人,顿时在怜爱之外又多了一份尊重。文清在青花镇无依无靠,青花内心深处的大姐情怀自然被唤起,义不容辞地认她作了妹妹。而林麟与她也非常投缘,丝毫不把她当作陌生人,很快与她亲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