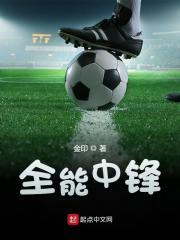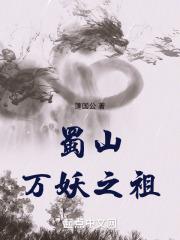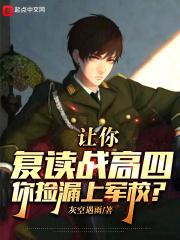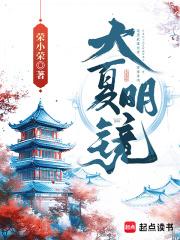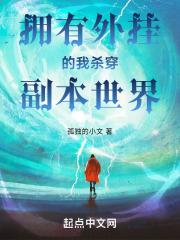在曹家堡静静享受美好的和平时光,每日里只是很规律地生活,每天出去遛马,偶尔出去打猎,生活优游闲适,只是偶尔为儿子们操心一下。至于政事,我尽量交给部下们去做,实在没有先例或者棘手的难题,才自己出动搞一下。
很多人觉得有特别好的人才主君就可以省力气,其实不然,有好的制度才是最重要的。个人再能干,不免也会有些纰漏,而制度较完善,即使部下们才干略差些,也一样干得很好。有好的制度,有完善的行为准则和习惯法,比起某一个难题具体怎么解决,或者有什么奇思妙想要重要得多。
一个很鲜明的例子是齐桓公和晋文公两个人的比较。两位主君的才干和胸襟都差不多,晋文公手下众臣,没有一个比得上管仲的,两国的继承人,晋国的继承人(我忘记两个继承人的名号了)荒诞无耻,也比齐桓公的儿子差得多,但两国的结局截然相反。管仲执政数十年,他死了之后齐国就迅速衰落,而晋文公执政不过十年,不但称霸当时,各国服从敬畏晋国做盟主还持续了一百多年。道理非常简单,因为管仲虽然能干,却朝令夕改,没有惯常做法,没有形成好的制度,结果他死了之后人亡政息,又恢复了原来的混乱局面,而晋国虽然没有特别出色的大臣,但正因为如此,晋国的老臣们小心持重,非常谨慎地建立了非常好地制度和规范,按照这一套老习惯,晋国在晋文公辞世之后依然能够称霸天下。
同样,唐玄宗开元时期两个著名的宰相姚崇和宋憬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姚崇被称为“救时之相”,处理具体问题迅速而且妥当,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日里都忙忙碌碌毫不得闲,把政务处理得很好,而宋憬截然不同,他看上去非常散漫闲适,雅量高致,从不出任何奇思妙想解决问题,而更多的关注官吏的人选和法制的完善,结果虽然看上去很懒,但实际上管理国家比姚崇干得好。所以真正当宰相的人,应该是性情稳重胸襟开阔的人,为百年千年计,为万世开太平,而不计较于一时一事的得失。所以在我看来姚崇那种人不算是真正的宰相之材,真正的好宰相应该是宋憬。那种把部下们的工作抢过来自己做,显示自己才华和勤奋的固然是人才,却当不得“大才”二字,但往往这种人名气更大,因为他们看起来更有才华。这就像武将一样,那些打得乒乒乓乓百折不回、千里兵疯,万里血漂的将军并不是真正会用兵的将领,反倒是那些悄无声息,轻轻松松的消灭敌人的将领才是真正的名将。这也就是所谓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道理了。管仲死后,齐国陷于混乱,人民更加怀念管仲,但实际上呢?齐国的混乱,管仲是要负上责任的,最起码他连一个好的继承者都没有找到,这样的宰相有什么用?但人民就是怀念他,他的名气反而更大了。
我们国家古时候有一个寓言,说有一户人家的烟囱建造得不对,容易着火,有人建议他改建,那户人家不听,结果后来果然着火了,邻居们都来帮忙救火。等到火灭了,那户人家摆下酒席,坐在上座的是那为了救火而烧得焦头烂额的邻居,而不是那个指点他改建烟囱的高人。这就像是治国,其实论才干,论杰出,自然是那个指出烟囱造得不对的人更高明,可是名气呢,往往是那个救火的家伙名气大。历史就是常常跟我们开这样的玩笑。
但我既然有这样的觉悟,处理政务的时候自然也有所取舍,更多的侧重于建立良好的规章制度,而不是如何更巧妙地解决问题。问题的解决有时候依赖于天才的想法,但天才是未必随时都有的,即使有,人的才干也有其极限,我们决不能寄希望与所有解决问题的人都是天才而且永不犯错,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制度要重要得多。没有大智若愚的制度的制约,往往好心的天才办的坏事甚至比坏心的天才办的坏事还更严重。从这个角度上说,其实后世的朱总理也谈不上“宰相”二字。就像解决贪污问题,不是靠监督一下,抓几个贪官所能解决的,根本还要从制度上入手,改变不断产生和涌现贪官的机制,而不仅仅在于监督的问题。一面是有坏的制度,能够把好好的青年培养、引诱甚至逼迫成贪官,另一方面却又高喊反贪,抓到了贪官拼命杀,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有一个管仲式的天才,问题或许还能压一压,但管仲死了呢?问题还会更严重,甚至于因为管仲耽误了别人改革的时间和机会,实际上反而是造成了历史的反动。
总之看上去我很闲,但我自诩高明,豫州的百姓士林常常以为我日理万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我虽然需要殚精竭虑,为国家谋长远,但十几年来领地的政治越来越完善,所以看起来领土越来越大,事情越来越多,但我的实际负担其实是越来越少了。
七月初八,捷报频传大学里面又有了一次盛事,原来有几个研究热力学的学者大概觉得好玩吧,用金世集的胶水和棉布制造了几个热气球,经过了几次试验之后打算今天进行载人试验。他们先前用煤炭和木柴进行试验,结果失败了,后来我教会他们使用酒精,结果成功升空了几次。
我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到了大学,我们到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了,不过嘛我是主君,自然有一些特权,我也从不鼓吹什么这时代根本不适合的人人平等,老实不客气地坐到了留给我的最好的位子上。
学者们前几天已经成功地把一只狗送上了天,后来酒精烧光,又慢慢地落到了地上,狗也活下来了。这一次他们打算亲身体验一下,装了很多酒精进去。这酒精多是用番薯酿的酒提炼的,经过多次蒸馏得来。纯度大概在八成以上,完全可以燃烧。
广场中央摊着一个大热气球,旁边有一个篮子,大约可以站两个人的样子,绳子是比较粗大的棉绳,紧紧地绑在厚重的气球上。因为没有轻柔坚固的尼龙,热气球造得太大容易撕裂,所以这个热气球效率不怎么高,个头也不怎么大。篮子是用藤条做的,看上去手艺倒是很不错,做得很漂亮。棉布是要透风的,为了不漏气,在厚厚的棉布间抹了几层胶水,是金世集发明的那种用明胶、树脂和少量化学制剂的结合,略微改良了一下配方,使气密封性更好。总的效果来看达到了帆布的坚韧标准,只是略重些。
不一会儿学者们来了,看到我也没有迎上来,只是点头鞠躬致意,更加没有让我发表什么讲话,几个人走到热气球那里,其中一个人开始给观众们讲解热气浮力升空的道理,另一些人则开始做准备工作。有几个人扛来了几个大木桶,解释的人说里面是酒精。又抬过来两个特别的炉子,一个大一个小,大的那个装在地上,小的那个装在篮子里。
讲解的人说炉子是用来烧酒精的,他们把大炉子放到口袋下面,把火点到最大,不一会儿便看见口袋渐渐鼓了起来,一些人努力把热气往里面赶,气球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很快就把站在口袋上的人都淹没了,再鼓一会儿,口袋把上面的人撑了起来,那人已经站立不稳,从上面滑了下来。没有想到热气球能够把人在平地上撑起,周围的群众和学者们都鼓掌欢呼。
气球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它的固有形状也渐渐显示出来,是一个椭圆形的大气球,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口子,对准了篮子和火炉。气球离地的一刹那,引来了暴雨雷鸣般的掌声。
气球漂了起来,但藤篮子还是纹丝不动,大火炉继续加热,气球和篮子之间的绳子越来越紧绷,一会儿篮子就摇摇晃晃起来。学者们赶紧让仆人把小火炉和铅块装进篮子,又把篮子压住了。
在近十万人的万众瞩目之下,一个年轻的学者郑重地跨进了篮子,他只有二十岁的样子,决不会超过二十五岁,脸上一副又兴奋又庄严的神色,仿佛他就要一去不复返了。我这时候突然特别妒嫉起他来,因为他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飞到空中的人。这个年轻人好像叫做姜怀,后人们一定会记住这个名字,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先驱者。
篮子不远似乎有他的家人在那里摇旗呐喊,一位中年妇女热泪盈眶,似乎要和儿子诀别的样子。我虽然不懂得如何制造热气球,但看这个热气球的牢固程度,这位小伙子的生命安全还是相当有保障的,顶多是慢慢掉下来,不至于摔死。除非那个胶水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导致气球突然爆裂,不然大概是不会出事的。
气球越来越鼓,看起来真有扶摇直上的气势了,篮子也被拽离了地,地上拖着几根绳子拴在一个地桩上。篮子越升越高,所有人都鼓起掌来,就连我都站起来仰望着他。这一时刻姜环是主角,是中心,是居高临下的英雄,所有人都仰望着他徐徐升入天空。大概两分钟后跟地上连接的绳子也拉紧了,一个学者拿起砍刀砍断了绳子,气球猛地往上一蹿,从下面看上去,他几乎要和云彩一样高。
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人类终于挣脱了重力的束缚飞上了蓝天,无论是老人、妇女还是儿童,一个个都欢呼雀跃,我的儿子们看得热血贲张,曹冲脸上红彤彤的,似乎所有的鲜血都涌到了脸上,他的脸色本来就粉嫩粉嫩,这一下更是好看极了。一群小孩子冲出大人们的队伍跑到了广场中央的草地上,他们欢呼着,翻滚着,呐喊着,似乎很想自己坐上去逛一逛。曹冲看到其中一个小孩,也挣脱了他二哥曹昂的手,跑到前面去喊道:“诸葛亮!下一回我让爹爹给我们做一个!”
那个被叫做诸葛亮的小孩看到曹冲,说:“真的么?你爹爹也会做?”
曹冲昂起小脸得意地说:“当然!我爹爹什么都会,这些人做气球,也是我爹爹教的!”,看到诸葛亮似乎不太相信的样子,又补充说:“他们所有的本事都是我爹爹教的!”
等一等!那个孩子,他叫诸葛亮?我忽然反应过来,真的还是假的?他什么时候到豫州来的?居然还跟曹冲认识了!我眼睛顿时盯住了那个小孩。那孩子拖着鼻涕,身上脏兮兮的,衣服倒还整齐,而且是丝绸做的。我正狐疑间,曹冲却拉着那个诸葛亮的手走到我面前来了。
“爹爹!爹爹!~”曹冲跟我撒娇说,“我也要坐气球,我也要坐气球嘛!”
我却死死盯着“诸葛亮”,说:“你是不是有个哥哥叫做诸葛瑾?有一个弟弟叫做诸葛均?”
“你怎么知道?”拖着鼻涕的诸葛亮很是奇怪地看着我,“是冲哥跟你说的?”
冲哥?晕,我的头都大了起来,他们俩什么时候结拜了?
我的这个曹冲可不是历史上那个曹冲,历史上那个曹冲是很小的,而且很小就夭折了,我这个只不过比长子曹丕小了七岁而已,今年也有七岁了。看那个拖鼻涕的小孩果然跟冲儿年纪相仿,历史上的诸葛亮的确也是这么大。
曹冲却只是拉着我的衣袖不停地撒娇,我说:“气球嘛,太危险了,等你长大了些,到十岁的时候就让你去坐,好不好?”
曹冲虽然撒娇,却不是嬉皮赖脸的孩子——我家教素来是很严的。他“哦”了一声,拉着我的手又看起了天上的气球。
我问诸葛亮:“你是怎么认识我家冲儿的?”
诸葛亮却要抬头看天,显得很不耐烦,他说:“冲哥和我一起念书的。”说完就去看气球了。
我问曹冲:“冲儿,你们念书,谁念得好啊?”
曹冲却不屑地说:“每门课都是我好些,算术、文章、诗词,我每样都拿第一!”
诸葛亮听到曹冲的话,脸上颇有几分羞愧。曹冲又指着诸葛亮说,“不过他总是刚好在我后面,都差我一点点,我就做了哥哥了。”
我险些幸福地要晕倒,曹冲能够在我的教养下胜过诸葛亮是我所没有想到的,一向都以为诸葛亮大概是中国人里面最聪明的,不想我随随便便的一个儿子就能胜过他,真是太有面子了。不过转念一想,这两个孩子不过都是拖鼻涕的年纪,这一点胜负也说明不了什么,便不再放在心上。
晚上我亲自去拜访诸葛家,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接到我的拜贴十分惊讶,他现在是一个豫州的小官,好像是一位主簿,诸葛家家境还可以——我的官吏的薪俸是相当丰厚的。
我问起诸葛家怎么跑到豫州来,诸葛珪说是三年前从琅玡避难来到豫州的,本来想去南阳帝乡投靠亲戚,但路过豫州看到这里民丰物阜,生活安定祥和,而且看来我曹操也十分强大,有能力保守豫州,便在这里定居下来。
当时天下很多知识分子都万里迢迢慕名来到大学“瞻仰”求学,诸葛珪也是好学问的,自然也不例外。他谋了一个小职务,在大学里面担当了一个相当于高级文书的工作,生活倒还一般,不如在青州的官大,但主要好处就是能够浸淫在这里浓厚的学术氛围中,还能常常看到大师级学者们思想的碰撞,常常可以聆听大师们的教诲。
我听了诸葛珪的话这才明白过来,看来这“南阳诸葛亮”以后要改称为“豫州诸葛亮”了。但人的成长和他的经历密切相关,陈国诸葛亮未必就能成为历史上那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他智商很高倒是不应该被怀疑的,至少能够做一个学者吧,我心里想着,还是有必要好好培养一下。不过现在诸葛亮能够跟我儿子一起同班同学,在成长方面的条件也很难有更好的了,他们的老师是管宁的一个弟子,学问不是很高,但非常会教育小孩子,德行也很出名,名气还是很大的,不过是教教小孩子而已,就算是郑玄亲自上阵,也许还不如这个老师呢,教这么小的小孩子跟老师的知识水平其实关系不大的。
诸葛家三兄弟才干都还不错,我有心培养以下,又似乎没有画蛇添足的必要,便提出让诸葛珪去给我一个门客去负责一下家族牧绵羊产业的经营工作,这样他们家就能够住到曹家堡边上了。诸葛珪儒学不怎么样,但却是精通数学和天文学的,甚至积攒了一年半的俸禄买下了一个昂贵的小型天文望远镜(业余爱好者的那一种,不是牛顿反射式大型望远镜,那是个人买不起的,也没得卖)。这种精通数学的人才能教出诸葛亮那样的儿子,要胜任一点理财和经营那自然是绰绰有余的了。现在我的绵羊群增殖相当快,每个月都有二十多头新的小羊羔诞生。因为把这些绵羊当作宝贝来照料,并不计较成本的,所以现在还在往里面贴钱。
回到曹家堡,我依然唏嘘良久。造化弄人,竟然能够让曹冲和诸葛亮变成了同窗,还结拜了兄弟,所谓沧海桑田,也不过如此了吧。曹冲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关心诸葛亮,拉着我的手气嘟嘟的跟我睡在一起,不肯离开,连睡觉都说梦话要跟诸葛亮坐气球。我***着他嫩嫩的脸,一阵阵骄傲和温馨的感觉从心底浮了上来,很快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