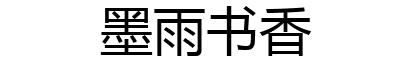(上)
在大学里我循规蹈矩,认真地上课做笔记,背着书包上自习,在学生会和社团里担任喜欢的职务,交形形色色的朋友,拿一等奖学金。
课余的时间我经常写信。长长短短,寄往那些对我来说无比重要的地方,告诉我爱的人们,我在一个遥远的角落里仔细地想念着他们。我也用QQ,用E-mail,用手机短信,可我还是喜欢写信。看蓝黑色带香味的老板牌墨水从我的钢笔尖溢出,渗到纸上一点一滴汇成横横竖竖的文字。
每周的第一个早晨我会拿着一个印着我的大学校门的好看信封走到宿舍楼旁的邮筒前,把它一点点塞进去。信封上的收信人名字是许夏。
我始终记得,我没有和他告别。或者我是在相信着重逢,所以不愿意让告别成为多余的累赘。
许夏偶尔会回很短的信给我。他说复读班的教室就是我们上高三时所在的教室,桌椅全是那时候的,人却面貌全非。许夏在班级里不爱说话,只用倔强的目光长久地凝望斑驳的墙壁。那应该是一个让我心疼的寂寞姿势。
我记得那些早已不再洁白的墙壁上留着我们的高三文化,一大片一大片,张扬着文科班的个性。我更记得在我坐过的靠墙位置旁的墙上,我用细密的字体写了两个好看的字:许夏。我想,如果许夏坐到我曾坐过的位置,会不会看到那一小块已经久远的痕迹。
当一切云淡风轻,似乎追忆曾经也成了太晚的余味。
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喜欢北京。这座繁华的北方城市有着阴暗的扬沙天气和蒙了一层灰的阳光。起风的日子会听到风声在窗外很张扬地摇摆。
昕昀的短信总是在半夜的时候过来,以至于我只能在第二天早上起床时才能看到她常说的那句话:“麟麟,要好好照顾自己,乖一点。”她将高三时落下的晚睡失眠习惯带到了大学,时常在半夜都睡不着,爬起来看书写字,或是发短信给我。这让我总是感到担忧。
我不再排斥音乐。我在等待着许夏在未知的一个时间来实现和我的两个约定。他几乎已经扫清了我的天空中关于音乐的那一块阴霾,我愿意为了他不再逃离我原本深爱着的一切。
因此我成了离学校不远的那家有着炫红颜色招牌音乐酒吧的常客。
酒吧的名字叫红蛊。两个设计奇异的字体在红得很纯粹的凹凸招牌上诡秘而艳丽。我喜欢这个名字,也喜欢这家平凡的小酒吧。我和阿蕨经常到这里来,坐一张偏僻的桌子,喝饮料,听歌,聊天。
阿蕨是一个有着纯净笑容的女子。我曾经武断地认为我在大学里不会再交到能以知己相称的朋友,但事实上我错了。我们在同一个学院,不同的班级和宿舍,相识于一间晚自习教室。那天我们相邻而坐,都没有带专业课本去上自习,而是带着同样的一本小说。无意间发现后,都笑了,然后很自然地聊起来。
我和阿蕨最平常的周末,便是在这里度过。我会带上一些杂志,阿蕨会陪她的男友童歌练吉它,写歌,唱歌。
童歌是学校的文娱部长,联合社团主席,比我们高两届,是有着雄心壮志的一个音乐天才。在我和阿蕨刚入学不久,他听到阿蕨在全校的歌手总决赛中唱歌,便放下了高傲的历届校园歌手冠军的架子,抱着吉它对阿蕨说我要为你写出最适合你的歌,而且要你做我的女朋友。
后来阿蕨在元旦晚会上唱了一首童歌写的《奇迹》,然后和童歌一样闻名全校。
我们最开始喜欢红蛊便是因为童歌。他在这里当兼职乐手,周末的晚上带着他的乐队过来。我和阿蕨是最忠实的观众。红蛊的舞台很简单,甚至是有点儿简陋。但当童歌出现在台上时,我可以阿蕨的眼中看到一个辉煌的光芒四射的舞台。
童歌每次演出的保留曲目,便是《奇迹》。他全心为阿蕨写的歌。
这个季节,在我眼里,只有你是最美的奇迹。我什么都可以放弃,为你唱出前世今生的意义。
童歌在台上深情地拨动吉它,似乎将全部热情都倾注到这一字一句里。我却经常恍然看见台上站的不是童歌,而是许夏。许夏。
从高三开始潜滋暗长却一直潜伏得太好连我自己都浑然不觉的隐秘情感,在已经远离之时却如同野草般疯长起来。我一直清楚我在许夏心里是怎样的位置。哥们儿,蓝颜知己,无人能替代的知音。但是现在,我明白我想要的不是这些名词,绝对不是。
许夏信中的只言片语变得越来越少,到后来竟然渐渐停了。我没有在意。我本来也并不希望他在辛苦的高三复读之余还要花费宝贵的时间来给我回信。
但是寒假过后,许夏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踪影。寄出去的信一封封被退回,信封上残酷地写着“查无此人”。除了母校的地址,我没有他的任何联系方式。我甚至一时间不知道应该打电话问谁。
可是我一定要找到他。我告诉自己,林麟你没有办不到的事。我动用所有的人际关系,包括并不太熟从未联系过的同学。一无所获。他本就是这样独来独往的人,断然不会告诉其他不相干的人他的行踪。
找不到许夏,生活还是要过的。晚上打篮球,打到筋疲力尽也不愿停手。晚上打球,是许夏的习惯,我从他那里学来。不大的篮球场,不多的人。对面楼顶的大瓦白炽灯的光毫不吝惜地洒到球场上来,使球场不至于显得太过黑暗。跳起来去抱球时,听到清脆的轻微断裂声。我疑惑地查看自己的手。蓄了多日被我精心修剪过的很精致的右手小指甲被篮球硬生生地撞断了。留下一个难看的断层,刺目而突兀。
篮球滚到我脚边,停下了。我摩挲着残存的指甲,却神经质地笑起来。
一段时间后,我终于还是知道了许夏在哪里。他毕竟不是生活在他自己臆想的世界里,终是被现实的一切所包围。我打听了所有的中学,得知他在母校附近的一所中学继续他的高四。其实我觉得自己很卑鄙。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许夏明明是在刻意地躲避和隐瞒,而我却不依不挠地追寻。昕昀说一切顺其自然不好么。可是我停不下来。
我摊开信纸想了半天,最后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了十个字。我终于知道你在哪里了。蓝色的笔迹,很清新。折好,放进信封,写上那个陌生的校名熟悉的人名,寄了出去。
这封没头没尾的信寄出后很长时间,我接到许夏的电话。又是五月,又将立夏。
“生日快乐。”许夏说。
“谢谢。”我平静地说。
然而他接下来说的话让我没办法再装扮成矜持的模样。“高考后,我要出来旅行。北京,行吗?”
我冲着电话大喊道:“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全然不顾教学楼的走廊上人来人往的目光。
他的声音里带着浅浅的笑意:“你的信吓了我一跳,林麟,你真厉害。高考后再给你打电话,再见。”
昕昀发来短信说,记住,他只是把它当作一次旅行。我没有回复。
六月很炎热。临近期末考试,自习室里人满为患,甚至因占座而吵架。每个人似乎都烦躁不堪。我在图书馆四楼的自习室里汗流浃背地温书。一大堆厚厚的教材让我几乎招架不住。思维里会出现短暂的空白,有时必须把已经看过的内容再次从头看起。
六月八号的晚上,我的手机在书桌上欢快地振动起来。家乡的区号,亲切之至。许夏说他不会食言,过几日,填完志愿,便出发。
几日后的那个晚上,我去火车站等待。到得太早,其实还有几个小时火车才能到站,而且还晚了点。火车站熙熙攘攘,霓虹闪烁变幻,我站在出站口的角落里渺小得像一粒尘埃,却充满了欢喜。
随后的几日,我逃了课陪着许夏。天气很热。北京的桑拿天让人容易烦闷。我说你应该冬天来,这里有四川很罕见的冰天雪地,你会很喜欢。他说生活中若是一切都遂愿,就不正常了不是吗。
他来履行两个约定中的一个。认认真真,为我弹了一次吉他,在学校操场的草坪上。我邀请了阿蕨和童歌,我们四个就这样席地而坐,许夏和童歌一人一把吉他,我和阿蕨聆听,偶尔和着旋律哼歌。
假如这只是梦境中的幸福,我愿长睡不醒。
去火车站买返程车票时我们有了分歧。我执意要他多留一天,他执意要买第二天的票。都是执拗到极致的人,在售票窗口前沉默地对峙起来。我挡住窗口,他拿着钱却没有办法递进去买到票。我们身后并没有别的人排队买票,因此售票的阿姨便也没有催促我们,而是笑眯眯地观看。我想她定是把我们看成了一对小恋人,这种误会倒也挺好,起码这一幕也许真的那样单纯和自然。
最终是我输了。在许夏面前,我从未曾赢过。
却也只能满足了。这座城市,从此留下他的印记。我还能怎样。
许夏并没有考到北方来,而是去了与四川毗邻的重庆,一座热情的城市。我仍然给他写信,不管他是否回复。
对于他曾经试图消失在我的世界里的举动,我们都缄口未提。这渐行渐远的距离,我狠狠将它视而不见。我还是相信着,我们从未道别。
其实如同我曾经告诉他的那样,爱一直都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曾经我天真地以为只是暂时,而这个暂时却狡黠地无限期延续下来。自始至终。
又一次听《奇迹》在悠扬的吉它尾音中结束后,童歌坐到阿蕨身边,玩了一会儿面前的啤酒瓶,说:“阿蕨,我有事跟你说。”
阿蕨翻着一本服饰杂志笑盈盈地点头。我看见童歌脸上的严肃神情,心里一紧,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我想退学。上海的朋友成立了一个乐队,请我过去当主唱,然后和唱片公司签约,然后……”
阿蕨的甜美笑容在嘴角僵住了。“可是你已经大四了,马上可以毕业,拿到学位证。”
童歌低头更小声地说:“是的我大四了,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我学的这个与音乐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对我有什么用。”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的。他说:“阿蕨,跟我一起走。”
阿蕨站起身拉起我的手离开了红蛊。没有回头,义无反顾。我不知所措地下意识回头,看见童歌求助的目光,却不敢正视那道目光。它承载了太重的梦想与取舍,关于音乐,关于爱,是我几乎无力承担的东西。
到了我的宿舍阿蕨才伏在我的肩头小声地哭了起来。
我感觉到心底深处的难过一层一层地浮上来。“阿蕨,他不会走的,他会留下来。”我的声音是那么空洞而乏力,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阿蕨清醒而坚定地说:“他会走的。《奇迹》里他唱道什么都可以放弃,可我太了解他,知道有的东西他不会放弃的。他一定会走的。”
“那么,你会不会跟他一起走。”我小心地问。
没有回答。
阿蕨沉默地拭去泪痕,拉开我的宿舍门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
收到妈妈的短信。简单的几个字。粉碎了这么多年来自以为平静而习惯的生活。
父亲回来了。
很多年前的一幕幕渐次清晰。从墙上摔下来的小提琴和突然断了弦的二胡,唤醒尘封多年的熟悉旋律。那个曾经在我心目中是伟大音乐家的男人,回来了。
我曾经猜测的那种结果原来是错误的。他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漂泊多年,一无所有。年华老去,终于疲倦,开始懂得生命中到底什么才最为可贵,于是不再躲避,回来了。一切竟然只是如此简单。
我无从揣测妈妈看见她曾经深爱却毁灭她的青春和婚姻的这个人再度出现在她面前时是怎样的心态。我曾在深夜里想了好久想到头疼,却发现我怎么也记不起来那张在我记忆里出现过很多次的模糊的脸。
妈妈打来电话。“女儿,他在外面吃了很多若。他的最大改变,是不再赌博,和知道了家的可贵。”
我握着电话,听到妈妈的声音平静如水,没有起伏的感情夹杂在里面。
我小声地问:“妈妈,你会和他复婚吗?”
没有回答。
我很困惑。不明白我的生活里为什么总有这么多的疑问。而所有的疑问又总是没有回答。
可我又是多么清楚地明白妈妈这么多年的等待。她从来都相信着他会回来。而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是我早已经忘却应该怎样用琴弓在琴弦上演奏出美妙的旋律。如果那把陪伴我度过童年时代的小提琴抖落年华浮尘重新摆放在我面前,我已经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姿势去拿起它。
童歌很快办好了退学手续。阿蕨果然多么了解他。
没课的下午我和阿蕨到红蛊喝咖啡。阿蕨一如既往的冷静与沉着。
“他还在试图说服我和他一起走。可是林麟,我们能否轻易放开一切,无牵无绊。”
我沉默地用力摇头。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音乐和文学一样,是爱好而不是梦想。我只想专心学好我的专业,拿到学位证。我也许还会考研,然后有份稳定而适合我的工作,可以好好孝敬我的父母。我向往的生活如此简单,可是童歌不能陪我。那么就彼此放开,期待各自的未来。”
我用力点头,不再沉默。“阿蕨,我懂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