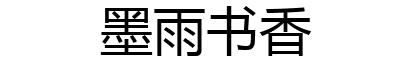(上)
我和易景轩平常各自忙碌,周末的时候,他乘坐地铁,穿越半个北京,从祟文门到海淀区来看我。他不止一次提出要我抽空和他回一次离北京只有两个小时车程的家,而我毫无商量余地地坚决拒绝。后来他怕惹得我不高兴,就再也不提了。
我有时候都会为我自己的执拗与古怪感到生气。和他回去探望他的父母,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我为什么非要这样抗拒?决定与他交往,不是醉酒后的胡话,我是真正想要珍惜这样的一个人,或许是听了许夏的话,不要因为他,而错过我真正灿烂的夏。可是我为什么总会莫名烦躁,常常无端地和易景轩吵架,滥用他的好脾气。我强迫自己不准再想许夏,但自己强迫自己的滋味,真的太难受。我分不清楚我内心深处的爱,这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情。报社的工作是我想要的,但我快要承受不住连轴转的高强度,北京鳞次栉比的高楼让我会有短暂的眩晕和窒息。我感到恐慌。
灿恬毕业后,凭着几年来在学校的优异表现和经常演出的经验,成都的一家艺术学校向她发出邀请,聘用她成为学校的一名声乐老师。田文亦在成都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他俩订了婚,开始按揭供房,安安稳稳的甜蜜小日子让所有人嫉妒。红豆树数年如一日,静静地变换了凋零与茂盛。而那些饱满圆润的红豆,从来没有改变过颜色。她一直是这样与世无争容易满足的简单女子,永远以灿烂的笑容面对生活给予的一切,生活有什么理由不对她慷慨?
昕昀,我那孱弱得像温室里的花朵的昕昀,在大四刚开始的时候,就休学去了西藏。她在大学里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男孩,他令她觉得拥有全世界。他愿意陪伴她实现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到西藏生活一段时间,无人打扰,安安静静,写作、旅游,仿佛世界上只剩他们两个人。他们果真这么做了。一年多以来,我经常地收到昕昀从西藏寄来的信件、照片、各种的小礼物。两个人在清澈得完全不真实的蓝天下相拥,我怀疑我高度近视的眼睛是否产生幻觉,然而不是。昕昀,我会听你的话,珍惜拥有的一切,跟随自己的心走,然后,像你一样幸福。
阿蕨与童歌,重新在一起。无论那座城市多么令人敬畏,两个人的力量,总会战胜一切。
散落天涯的花儿。但我仍然知道你们在哪儿,这是多么幸运。
又一个立夏的前几日,周末,易景轩加班,我们无法共度周末。天气很好,我在租住的狭小房间里,对着电脑郁闷。几首忧伤的歌循环播放,明明是我自己挑选的歌,听着听着却心悸起来,像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赶紧关了播放器,房间里于是一下子安静下来。
所以,当手机短信的提示声响起时,显得那样突兀,我被吓了一跳。
是妈妈的短信。内容有着天旋地转的力量。
沁儿死了。
他和几个小朋友到河边玩耍,一个小朋友落了水,他试图以他小小的力量去把小伙伴拉上来,却同样地掉了下去。其他孩子奔回家,不敢告诉大人,等三姨发现早已过了沁儿平常回家的时间时,已经晚了。
我握着手机,浑身颤栗。一定是在做梦。一定不是真的。我给妈妈打电话,要她告诉我这是假的。
但妈妈和林叔叔已经在赶往桐州的汽车上。她也并不十分清楚具体的情况,要赶回去了才知道。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声音在心里反复响起: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我甚至忘记了告诉易景轩。我以最快的速度订了机票,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赶往机场。这些事情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做出,而我的潜意识,还在一口咬定这是梦境,不是真实。
候机的时候,易景轩打来电话,我恍恍惚惚地接起来,才想起和他约好,等他加完班晚上一起去看电影。我的眼泪哗啦啦地掉下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急得快疯掉,好半天,我终于勉强和他说清楚经过,告诉他,我已经在机场,马上要回去。他抓狂了,喊道:“林麟,你等着,我跟你一起去!”
“不,我马上要登机了。我回去后会给你电话。再见。”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挂了电话,混乱的思绪在心里横冲直撞。我一片茫然。到底是真是幻。我用力闭上眼又用力睁开,却仍在这陌生的地方,独自一人,拎着简单的行李,等候登机。我只想赶快回到我最爱的家,去证实,一切都是梦而已,一切都很好不是吗。
熟悉的桐州。我在出租车上开始紧张和胆怯。这一次的归心似箭,和以往是那样的不同,要怎么面对?
我轻轻敲门,是三姨父开的门。我看到姨父明显憔悴的脸,看到苍老了好多的外公外婆,看到冷冷清清的家,心一下子痛起来。
妈妈和小姨在陪着三姨。我刚叫了一声“三姨”,泪便涌了出来。我不得不赶紧离开,走到客厅的窗边。一夜之间,三姨变了一个人。虽然心里早有预料,但是,看到三姨脸上的伤痕和泪痕,看到她陡然苍老的眼神和空洞的表情,我控制不住。
站在窗边,不敢看楼下的街道。从前,沁儿总是在街上蹦蹦跳跳,三姨平时喜欢在楼下打点小麻将。简单的小小幸福。可一切都变了模样。我们毫无预兆地经历这样一次悲痛的考验。是上帝嫉妒了我们的幸福,还是有意安排另外的际遇?我想不通,想得头疼,只能放弃。
后来我坐到三姨的身边,试图劝说,但我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劝说者。我说弟弟跟我们家没有缘份,让他去吧,至少这几年来,他是快乐的。我握着三姨的手,泪还是一直往下掉,泣不成声。我那么那么爱沁儿。一个悲痛的姐姐,要怎么去劝说一个最悲痛的母亲?
上帝就这样给了我们全家残忍的一刀。三姨在得知这个消息时,拖着摇摇欲坠的身体往出事的地点跑,谁也拉不住她。她在路上摔了好几次,脸上满是伤痕。三姨父最后强行把她带回家,不让她见到沁儿的样子。
忠厚善良的三姨父,沉默地做着所有的事情。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忙前忙后。他眼中隐忍的泪水,让我感到空前的刺痛。
要怎样,才能边痛边坚强。
亲爱的沁儿,他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孩子。或许,他本就应该是天使,不应来这纷乱的人间。他来过了,环顾了人间,觉得这人间有太多伤痛与丑恶,便揣着这几年来和我们全家共度的幸福时光,满足地回到了天堂。
弟弟,姐姐只能这样说服自己,才能让心里的伤痛显得平静一些。因为哪怕我向上天大叫一万声“不公平”,也唤不回你了,要我怎么释怀?我们全家从没做过任何坏事,都是善良到极致的人,你的爸爸妈妈,在老家和桐州,都是有口皆碑的大好人。命运这样的不公,我们要找谁理论?
眼泪只能自己慢慢擦干,伤痛只能自己慢慢抚平,因为清醒之后,我知道这不是梦,弟弟,你已不会回来,而我们,还得继续坚强。
那天下午,我们围坐在一起,姨父坐在三姨身边,紧紧握住她的手,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当我们现在刚结婚,一切从头来就是。
这是我听过最动人的爱情宣言。
那是如此煎熬的几日。
一个夜里,也不知道是怎样开的头,她们姐妹几个聊起了小时候的趣事。那个时候的日子过得很苦,为了可以吃饱肚子,她们都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现在听来,虽然有些心酸,但更多的是一种一起吃苦的幸福。小姨和妈妈都“招供”了好多小时候的经历,逗得大家忍俊不禁。我边听边看着三姨,突然,我发现她也笑了!小时候的回忆和趣事,让三姨笑了,虽然笑得艰难而不易察觉,但她终归是笑了。她笑了,我却差点哭了。
亲爱的三姨,对你的爱,竟让我不知如何表达。我很惶恐。我们之间多年的快乐方式,突然不适用了,于是我连抱抱你的勇气都没有了。我心疼沁儿,更心疼你。手停在半空,泪停在脸颊。爱也许不需表达。
立夏。三姨突然对我说:“麟儿,生日快乐。”
我泪流满面。如此巨大的伤痛面前,她,还记得她的外甥女的生日,要说一声生日快乐。初三那年,在大尖与她共度的日子在眼前晃啊晃,宛若昨日重现。
妈妈向学校请了假,暂时留在桐州陪伴三姨。我亦向报社请了长假。遥远的北京,乱七八糟的工作,都给我一边儿去吧!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蓦然跳了出来。或许,这个想法,早已埋藏在心底,只是终日麻木的生活,让我自己都忽略了它。是的,我想回四川了。北京,我多年的梦,当我正在开始将它变成现实,却一下子疲倦。我抛弃了故乡,以为自己很骄傲,如今却又想回来。
到底什么,才是最为重要的珍贵。
将这个想法告诉妈妈后,她的眼里,好像闪过了一丝明亮的光辉。我不太确定。她仍然和从前每次一样,没有对我的想法做任何评价。“不管你要做什么,妈妈都会支持你。只要你自己想清楚。”她不想阻碍我远行的脚步,此刻当然更不会拒绝我回来。其实,她一直都是希望我回来的吧?当我远行,千里山岭,她何尝真正地放心过?
易景轩每天打无数个电话,问我何时回北京。我心乱如麻。到底要何去何从。我似乎怯懦了。
上帝的安排,任何人的力量都会显得渺小不堪。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地动山摇,世界在一瞬间改换了模样。
桐州离震中很远,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但这场人们从未经历过的地震,足以令所有人惊惶失措。舅舅的公司暂停营业,小雪的学校停了课。住在高楼里的人们离开家,到体育场支起帐篷。舅舅想方设法抢购了几顶大帐篷,将全家人都安置下来。
万幸的是,在这场大灾难面前,我们全家,在一起。重庆的大舅舅一家,电话报了平安。在沿海打工的二姨,亦打来电话,确认全家人的平安。
给灿恬打了无数次电话,终于打通。成都受波及较为厉害,还好她和田文都平安无事,只不过也不敢回家,跟随大流,在外面搭帐篷睡觉。
昕昀老家的房子被震成了危房,在火车刚刚通行的第一天,她便风尘仆仆地从西藏赶了回来,陪伴她的父母和爷爷奶奶搬出旧房,暂居在帐篷里。
阿蕨从上海打通我的电话时大叫:“林麟!老天保佑,我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前不久刚知道你家里出事回了四川,我这颗心还没放下呢,结果恰好又赶上了地震,打了一天的电话也打不通,我快急死了!林麟,你还好吗?全家都还好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听见她在电话那头竟然开始泣不成声,我握着电话的手僵在空气中。
“林麟,关于地震的所有消息,让我无法接受。我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失去。林麟,你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一切都会好的,我命令你一定要健康平安,不许出任何事!”
阿蕨。我也希望如此。而且一定会尽力做到如此。
一夜之间,无数的妈妈,经历了和三姨一样的丧子之痛。无数的家庭,感受了和我们全家一样的失去亲人的痛彻心扉。上帝心血来潮玩了一个轻易的游戏,俗世的人们如何承担得起。
当易景轩终于打通我的电话准备和我说好多好多话时,我平静地打断了他:“景轩,我没事,家里也都很好。可是我必须告诉你,我不回北京了。我留在四川。这里才是我的爱所在。等这场灾难稍微平息之后,我去成都找工作,就此留下。”
像是过了一个世纪般漫长。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挂了电话。这太不像他的风格了。我对这段感情的不重视和不负责,定是让他伤透了心,完全失望了吧。这本就是我想要的结果。
我心中却没有想象中的轻松和释然。放弃一个人,放弃一段感情,放弃一座城,对我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为何我感觉到心里压着一块重重的铁,快要喘不过气来。
两个月之后。一切仿佛归于平静。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前往成都。
成都的一家报社接受了我在网上投递的简历,给了我三个月的试用期。灿恬帮我租好了房子,开心地等待着我。
我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比起北京的千山万水,仅三四小时车程的成都,实在是让他们能够放心。我们可以紧紧相依,不必再在天涯,牵肠挂肚。
在火车上我很快入睡。连日来心力交瘁,睡觉也总不踏实,可我居然在火车上睡了一个香甜无比的觉。梦中,许多故事一一浮现,真实而又遥远。小提琴、二胡、满书架的书籍、清华园、北京……
这些名词,交替着在我生命中演绎出或黑暗或明亮的色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梦想,却被我逐一放弃。
到最后,一身轻松,仿佛找到了救赎。
成都。我以惊人的速度在这座城市找到归宿感。我很快融入到它的节奏。震后的成都,依然是那座著名的美丽而休闲的城市,这里的人们,依然是乐观、积极、懂得享受的人们。在城市的繁华地段,春熙路、盐市口,以及公交车的站台,到处可以看见“因为有你,成都更美好”的宣传画。张靓颖、洁尘、谭乔、孙静,四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代表着成都不同的人群,共同代言成都,向所有人宣告着“因为有你,成都更美好”的坚定决心。每每路过这样的宣传画,总会有莫名的感动和自豪从心中升腾起来。
爸爸来成都出差之前,打电话给我,小心翼翼地想要约一个时间和我吃顿饭。我答应了,他很高兴,像个小孩一样反复确定时间和地点。或许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以为我会冷冰冰地拒绝。
我自己都有些奇怪。我一向认为我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这次,却开始混淆不清起来。自从爸爸回来后,林家人——我实在不愿意将他们叫爷爷婆婆——也给我打过电话,我从来没有接过。我是林风的女儿,这一点,确实无法改变,而且,我似乎已经原谅了他,这让我觉得惊讶。但林家人多年的冷漠和对妈妈的伤害,我不知道我需要多大的胸襟,才能将那些往事全部勾销。
他结束了他在成都参加的会议后,我们如约见面。
那天晚上六点过,我从报社去东大街,但我找了几圈也没有找到他的宾馆。很累,于是坐在路边不想走了。他打电话来问我在哪里,我说了我的位置。他可能是在宾馆的前台打电话,前台的服务小姐于是试图给我指路,我却没有好气地说我不想走。他连忙在旁边说没事没事我过来找你,你就在那里呆着别动。
我于是坐着等待。心里竟然冒出来心安理得的意思。这是他欠我的宠爱和言听计从。
是他先在人群中认出了我。唤了我的名后,我抬头,看到他。这是长达十年的分离之后我们的第二次见面。仍是陌生,对我而言他仿佛只是一个普通的长辈。走在他身边也只是沉默,他问什么我答什么。
晚上在刘一手吃火锅。他给我夹菜,我有些不习惯,因为这是记忆中从来没有过的动作。我闷头只顾吃饭,他在一旁说了很多话,我默不作声地听着。
他说的话,我其实都还听得进去。那么多年的沧桑流浪,他吃了不少苦,得了不少教训,但我无法释怀的是,现在的受益者,却不是我母亲。
对那些年的一切,他绝口不提,所以我仍然不知道他在沿海的那些城市究竟经历过什么。关于他的工作,和再婚的情况,他倒是坦然提及。这几年他很努力地工作,四十多岁的年纪了,和年轻人一样从底层一步步往上爬。他努力地想要鼓励我开始新生活,想告诉我职场上的一些经验,以及生活中的道理,但似乎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来讲述。其实我懂得。突然面对已经二十多岁的女儿,交流和沟通,定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而我最感兴趣的不是那些。中间我开口,岔开了话题,问:“你还拉二胡吗?”
他似乎有些惊讶,过了会儿才反应过来,说:“二胡我从来没丢弃过,一直在拉。”
我便兴奋起来,说:“我一直都很想把二胡重新捡起来,但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而且已经完全忘记了如何拉。”
他说:“有机会我再教你,很快就会想起来的。”这句话说完后却冷了场。有机会吗?
多么怀念那个年幼的孩子在做完作业的黄昏时分,认认真真拉着一首二胡曲的模样。
然后又说到了小提琴。他问我记不记得练小提琴时几岁,我说三岁吧,他便笑起来。
“还不到三岁呢。当时我专程跑到桐州去买二分之一的小孩专用琴,跑遍了整个桐州,才发现了独一无二的一家琴行,里面有独一无二的一把二分之一小提琴,价钱好像是100多。”
我便着实吃了一惊,80年代末的100多块钱,是他几个月的工资。
他明显陷入了回忆之中。
“那时候为了练琴我还打过你。当然不是真打,只是吓唬吓唬你,希望你从小养成做事情要坚持下去的好习惯。小提琴摔坏了之后,没有办法修,也买不到同样的二分之一小提琴了,于是就放弃了。而我的想法是让你练二胡,毕竟我对二胡更为喜欢,也更为精通。二胡你也学得很好。要是一直练下去……“
然后都没说话了。沉默。是他的离开让我不得不荒废了二胡,这点我们都记得,都明白。
还谈及五岁那年在篮球架下受重伤得了脑震荡并且险些毁容,六七岁时候莫名肚子痛被误诊为急性阑尾炎连夜送往凌县医院。这些都是妈妈早就讲过的故事,于我来讲早已是刻骨铭心,而这次从他口中讲出来,竟有了另外的感触。
原来这一切,他亦同妈妈一起经历,亦深深记得。那年二十多岁的年轻父母,彼此依靠,为自己患病的小女儿束手无策四处奔忙。原来在我们三个人的生命中,那些都是从来不曾忽略过的绚丽演出。而带着血缘的生命,在偏离轨道的多年,仍然纠结而有着交集,无论如何无法抹去。
那些爱恨,到底怎样才算是真正释怀。
他离开之前,我轻声叫了一声“爸爸”。十几年未曾叫过的这个名词,再次从我口中说了出来,陌生,别扭,却又那样的习惯和自然。他惊讶地看着我,努力抑制着表情的波动。
爸爸。我想我已经真正地长大。
炎炎的夏日周末。我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跟灿恬讲电话,死缠烂打要去她家蹭中午饭。田文做的一手好菜,对于我这个从来不下厨房勉强会煮方便面的单身女子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诱惑。灿恬佯装生气,发誓一定要手把手亲自把我教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慧女子,我捧着电话哈哈大笑。
挂了电话,我在屋里起劲地描眉画眼,准备去灿恬家。
敲门声响起。
我就是自诩聪明到极致,也绝对没有想到接下来我会看见谁。
易景轩。
他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站在我面前,汗水沿着发梢大颗大颗往下滴。
我张口结舌,甚至使劲揉了几下眼睛。
“是不是太久没看见帅哥,眼前一亮,隐形眼镜快要掉出来了?”他还是那样的嬉皮笑脸,拎起行李就往里走,全然不顾呆呆站在门口的我。
我的天。我一定是在做梦。
他一把搂过我。“林麟!你给我听好,我叫易景轩,是林麟的男朋友!林麟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林麟的梦想,我奉陪到底!北京又怎样,成都又怎样,我是宇宙超级美男子,我有霹雳无敌的双手双脚,在哪儿都可以给林麟一个天堂!”
刚刚画好的眼睛,被泪水冲得乱七八糟。毫无疑问,林麟现在很像一只脸上布满了感动的大熊猫。
“唉呀这样可一点都不好看,赶紧给我弄漂亮点儿!林麟你别说,成都美女还真是多,我这一路走过来,真是看花了眼,你得有危机意识知道不?……”
他滔滔不绝,我重重的一拳挥过去,他立马闭了嘴。
我就含着泪得意地笑起来。
他不是意气用事的男子,因此相隔数月,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才给了我这个惊喜。他通过努力,终于得到公司的同意,将他派到了成都的分公司,连户口,也一并转了过来。
从此相守,不离不弃。易景轩,我终于对你许下了一个诺言。
(下)
热闹的正月初一。几辆小轿车在门河村口停下,惹来村里人好奇与羡慕的目光。王家祖孙三代二十几口人,回来给淑珍上坟了。
熟悉的小河与山川。老黄牛在山坡上,悠闲自得地吃着草。路过一些田地时,莲桂会指着它们告诉林麟:“麟儿,你还记不记得,这些田地,以前都是我们家的啊!唉,可惜啊,现在都交给别人家来做了……”
胜利自然会瞪她一眼,说道:“你这个老太婆,老提过去的事干啥?现在谁还稀罕这些田地啊?你要是想回来种地,那就回来吧!只怕你儿子女儿不同意哦!”
晚辈们在他俩身后,开开心心地笑起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大家早已熟悉他们这样的爱情。平淡无奇,却比金坚。
青花和林安平,恭恭敬敬地在坟前跪下,磕了响头。
婆婆。这个家,因您而生,因您而爱。幸福与欢笑,一并分享;灾难与痛苦,一并承担。您在天堂,一定会认得您疼爱的曾孙子沁儿,您要照顾好他,亦要庇佑您在人间的子孙,安康美满。
爱,总是会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绝无改变。
哪怕生命终有尽头,那些或悲或喜的故事,与爱紧紧纠结,便成为没有终点的剧本。
不仅仅,属于青花。
后记:亲爱的各位读者,由于前段时间《青花》要出版,所以大结局迟迟没有传上来,至今,《青花》已经顺利出版,十分抱歉,今天才想起来,将大结局传了上来。感谢各位读者一直以来对林悟和《青花》的支持,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青花》的实体书!林悟会继续写下去,带给大家更好的作品!